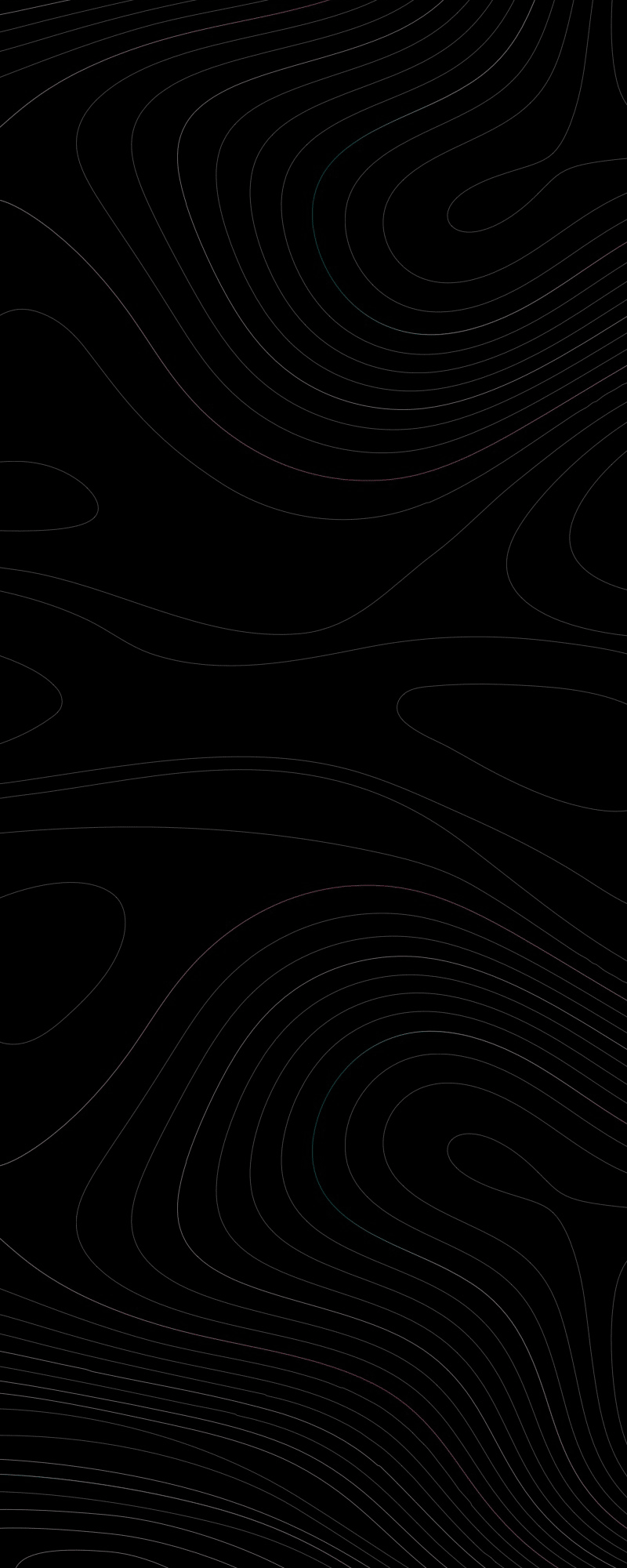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演员而已。他们有他们的出口和入口,一个人在他的时代扮演着许多角色。
– 威廉·莎士比亚
《如你所愿》,第二幕,第七场
大约一年前,我和家人去参观了大师草间弥生在安大略美术馆成功举办的展览——《无限的房间》。包括我们在内,那天的展览吸引了数千名参观者。参观者通过每个装置的节奏都经过工作人员精心的设计。沿每个装置绕行大约需要20到30分钟,之后在每个盒子内停留30秒。六个装置的体验时间加起来有两个半小时。我和家人觉得每一个装置都很棒,而其中,毫无疑问,“无限的房间”最为惊艳。
就和那天参观展览的其他所有人一样,在短短的30秒内,我们不停地自拍,只为拍出几张我们认为比较完美的照片。我们很擅长这项技术——架起手机,摆好姿势,然后点击拍照。
由于草间弥生的这些作品在“朋友圈”大热,人们很容易就忽略了作者的创作初心。早在数字化时代之前,草间弥生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进行“无限房间“的创作。实际上那是早在人类登月以前。如今,很难想象没有手机作伴的草间弥生体验展会是什么样子
那一天,拍下完美的自拍照并把它们发布到网上显然是人们最大的动力,而且这种动力甚至是不可逆转的——这对安大略美术馆来说无疑是大有裨益。那些日复一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和分享的内容以一种传统营销手段永远无法企及的方式,使更多的人前来参观。

所以是双赢,对吧?
在草间弥生展览之后大约过了6个月,我们一家人又去了位于多伦多的“快乐之地”,这是一个巡回展览,那里的每一种颜色、质地、视觉效果和展出设置都像是为“朋友圈”量身定做的。一样的排队、手机、自拍。这次不再是“无限的房间”了,我们坐在一个黄色的浴缸里,周围是成百上千只黄色的鸭子。与草间弥生展览不同的是,我们在“快乐之地”呆了两个小时,却觉得空虚,反倒没有那么“快乐”。
近日,《艺术报》提出了一个不无道理的问题:既然社交媒体上的分享对展览的人流量愈发重要,那么展览策划人难道不应该在主题、展品选择和展览设计上最大程度地迎合社交媒体的分享需求吗?
这让我有种让“特洛伊木马”进来的感觉。二十年前我去卢浮宫的时候,《蒙娜丽莎》的前面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我只能透过肩膀之间的缝隙凝望那神秘的微笑。这样的游客体验不太好。而现在的卢浮宫,你大概会看到更多的人,只是他们的姿势全都是:背对名画,伸开手臂地自拍。
营利性“博物馆”早已存在,比如“快乐之地”、冰淇淋博物馆、幻想博物馆、“捉迷藏“——尽管内容各不相同,但模式都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旨在创造出照片上可展示的娱乐空间,使之成为我们线上生活的背景板。
不仅仅是博物馆在努力应对这些干扰。主题公园对手机游客的态度也很矛盾。我自己也有过亲身经历。有了手机的陪伴,在迪士尼两个小时的排队时间就变得不那么漫长了。然而,在手机上度过的那两个小时——阅读新闻、查看脸书、预订晚餐——把我从迪士尼的魔法中完全剥离。可是,不正是为了让我沉浸于迪士尼的这种氛围,这座乐园才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高额的投入吗?
所以是为什么草间弥生展览能令人感到愉悦而 “快乐之地”却不能?而且我为什么会如此怀念没有手机打扰的迪士尼时光呢?
一个伟大的博物馆和一个伟大的主题公园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有一种力量,能把我们从自己的世界中拉出来,把我们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我们带到不同的地方去。这是主题公园或博物馆的最大卖点。我们会接触到之前不曾想象过的故事、想法和经历,这种时候,个人故事也会变得不那么重要。
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两种范式的碰撞——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自我中心与博物馆和主题公园所提供的我们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我希望博物馆和主题公园能以此作为行动的主旨,在它们擅长的领域加倍努力——提供让我们把头从手机上抬起来的美好体验。

它将去往何方?
可能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初始阶段,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朋友圈”时代的浅薄将会演变成更丰富的东西。令我想到的是19世纪90年代电影工业刚兴起时的一个故事(可能是杜撰的),当时观众看到屏幕上的火车头飞驰而来会感到十分惊慌。那时的电影简直是一个奇观。从那以后,电影经历了最初、稚嫩、奇观的阶段,逐渐发展成为我们目前所熟知的丰富的叙事艺术形式。也许20年后,当我们再回顾“朋友圈“的这个时候,也会这么想——这就是历史时钟上的某一刻度,代表着某个最初的阶段,而从这个阶段开始它会逐渐发展成为更为美妙的东西。